2025 年 8 月 22 日,美国财政部以 89 亿美元收购英特尔 9.9% 的股份,一跃成为这家半导体巨头的最大股东。这一举措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激起了千层浪,因为这是非危机背景下,美国政府首次以股东身份介入高科技产业,标志着自由与干预的边界被悄然推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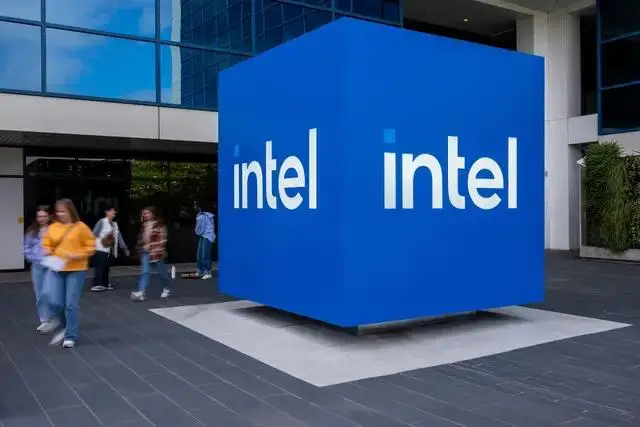
对于一向以 “自由市场” 为傲的美国来说,这一画面无疑极具冲击力。英特尔作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关键力量,不仅是美国军工体系、人工智能运算以及能源与通信安全的战略支柱,更是自由市场体制下科技创新的象征。然而,此次美国政府却以 “国家安全” 之名,堂而皇之地进入英特尔的股东名册,打破了以往政府极少直接持股企业的惯例。
回顾美国历史,政府在企业面临危机时的介入往往是临时的、救助性的。1979 年,美国政府为拯救克莱斯勒提供了 15 亿美元联邦贷款担保,2008 年金融危机时对通用汽车和 AIG 的注资也都是以解决危机为目的,危机过后政府便逐渐退出。但英特尔不同,它并非处于生死边缘,美国政府的入股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救助,而是一种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长期性参与。
这种新的战略逻辑将经济竞争直接与国家安全挂钩,把英特尔这样的高科技企业视为 “不能失败” 的战略资产。美国政府不再用 “市场失灵” 等传统理由来解释其行为,而是强调半导体产业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从而为股权干预赋予了正当性。这一转变意味着美国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以往的间接调控转向直接参与。
美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一方面,《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批评其 “撕裂自由传统”,一些保守派人士警告称这违背了自由市场原则,可能导致英特尔的决策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多干扰。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更是指出,《芯片与科学法案》中并无授权政府购买英特尔股票的内容,政府与私营公司的这种勾结会引发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也有支持的声音认为,这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支持航天、国防工业的逻辑相似,是一种 “国家安全例外”,并非对自由市场的根本背离。布鲁金斯学会与 CSIS 的评论甚至将其视为特殊领域下的金融工具创新。
从制度层面来看,美国并非没有对政府权力进行约束的机制。司法层面,1952 年的扬斯敦钢铁公司诉索耶案确立了行政权不能凌驾于国会立法和私有产权之上的原则,为政府干预企业划定了界限。此外,美国政府在此次入股英特尔时,虽成为最大股东,但并未获取董事会席位和特别表决权,只是作为一个被动投资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制度设计的克制,避免了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
然而,尽管有这些 “防火墙”,美国政府入股英特尔仍然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的担忧。如果以 “国家安全” 为由可以随意介入企业,那么自由市场的边界将变得模糊不清。而且,此次美国政府的举动可能只是一个开端,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透露,联邦政府可能会仿效对英特尔的股权投资模式入股更多企业,并涉足更多领域。
此外,英特尔将近 80% 的收入来自美国之外,美国政府的入股可能会给其国际业务带来诸多麻烦。其他国家可能会对英特尔进行更严格的外国补贴审查,在招标或投资方面设置更多附加条件。同时,由于芯片被列入军民两用清单,其他国家可能会将英特尔视为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企业,从而在进口和合资等方面设置苛刻的许可证要求。
美国政府成为英特尔最大股东这一事件,是美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它既反映了美国对半导体产业等高科技领域的高度重视,也暴露了其在国家安全与自由市场之间的权衡与挣扎。这一事件的影响深远,不仅将改变美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模式,也将对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以及自由市场的理念产生重要的冲击。未来,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一战略逻辑的发展演变,以及它将如何塑造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与政治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