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上海,蝉鸣裹着暑气。一位在高校深耕软件工程的教授朋友收到我的新书《工具的苏醒——智能、理解与人工智能的本质》后,发来一段微信对话,意外撕开了当前AI讨论的表层迷雾。
“您书中很多观点让我共鸣。”教授开门见山,”我是AI悲观派——现在的AI不过是重复劳动的’工具人’,复杂问题尤其是需要原创编码时,错误率高得离谱。”我回应:”总有人为利益神话它。”教授则感慨:”计算机界分两种人,搞理论的多是乐观派,搞工程的反而更务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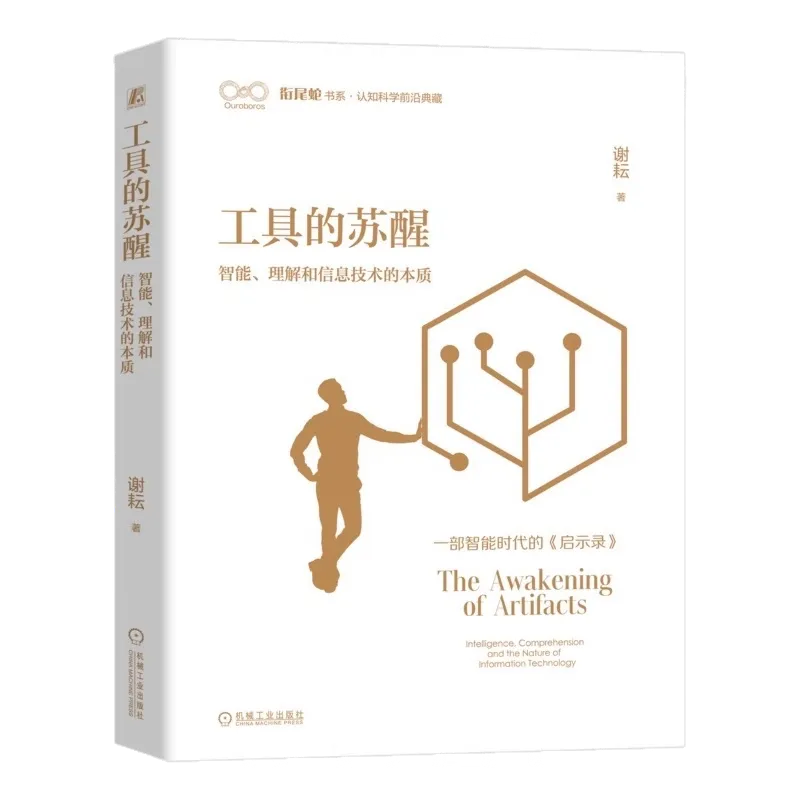
这段对话像一根引线,很快引燃了我对另一场”AI盛宴”的审视。七月底,一位专注投资与产业研究的朋友转来图灵奖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双料得主杰弗里·辛顿的AI演讲材料。作为学界”顶流”,辛顿的出场自带光环,可当我通读讲稿,却忍不住皱起眉头——那些被反复强调的”突破性观点”,竟充斥着逻辑漏洞与主观臆断。
“智能的本质是推理。”辛顿在演讲开篇断言。这让我想起教授提到的”AI乐观派”特质:用个人信念替代科学论证。从牛顿的万有引力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科学史上的重大突破无不始于对世界的”洞察”,而非单纯的逻辑推演。若智能的本质真是推理,那人类最珍贵的”洞察力”该往何处安放?更讽刺的是,辛顿的讲稿与几天前在英国的发言一字不差——正如朋友所言:”他是’走场专家’,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双奖得主’的名号能吸引眼球。”

这场”走场式”演讲的危害,远不止于浪费听众时间。作为科学研究者,最基本的职业操守是”实事求是”,而非用主观意愿曲解科学事实。这让我联想到写作新书时与一位AI学者的讨论:对方直言”大语言模型没有理解能力,只懂数概率”,虽有一定道理,却失之武断。人类理解世界靠的是多重关联——因果、符号、现实映射的复杂网络;而大语言模型的”理解”,目前仅停留在文字符号的统计关联层面。它或许能模仿人类对话的”外壳”,却永远无法触及”符号与现实对应”这一理解的根基。所谓”与人类理解非常相似”,不过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臆想。
从科学史的维度回望,AI的”理论困境”更显清晰。图灵测试作为AI领域的”奠基性工作”,本质上是主观的行为测试,违背了科学最基本的客观性原则。直至今日,人类仍未建立符合现代科学规范的智能理论——甚至连”智能是什么”都尚无定论。辛顿的”推理本质论”之所以站不住脚,恰是因为它试图用单一维度(逻辑推理)概括智能的全部内涵,这本身就是对科学复杂性的简化。
再看技术层面,AI的”繁荣”更像是一场”经验主义的胜利”。当统计方法借助计算机的暴力计算在应用层面大放异彩时,许多人误以为这是”科学突破”,实则是传统工匠技艺的现代升级。那些关于”AI发现物理定律””Sora是世界模拟器”的惊呼,本质上是对统计规律的过度解读——若统计就能发现科学定律,牛顿、爱因斯坦的贡献岂不成了”概率游戏”?至于”通用人工智能即将实现”的喧嚣,更像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集体幻想,与真正的科学幻想(基于已知原理的外推)相去甚远。

从信息技术的全局视角看,AI不过是人类拓展自身能力的工具之一。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早超越人类,但这从未动摇”人类是万物之灵”的地位——正如望远镜延伸了我们的视觉,显微镜拓展了我们的观察边界,AI的价值应在于辅助人类解决更复杂的信息处理问题,而非”替代人类”。那些渲染”AI威胁论”的言论(如辛顿”养虎为患”的比喻),不过是历史上”技术恐慌”的翻版,既无科学支撑,也无现实依据。
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边,我们更能看清AI的定位。现代科学诞生前,人类靠经验积累技术,发展缓慢且充满偶然;如今,AI作为”信息时代的工匠技艺”,虽能处理更复杂的信息问题,却始终无法突破”经验性”的局限。我们制造不出真正理解人类的机器,不仅因为大脑仍是”黑箱”,更因为现有科学理论尚未触及意识的本质。那些宣称”AI将超越人类智能”的预言,本质上是对科学边界的越界。
辛顿的双奖光环与”走场式”演讲,折射出一个危险的信号:当科学被流量与名气绑架,当”权威”的言论取代严谨的论证,科学的真理性正在被稀释。在这个”后科学”时代,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是:伪科学披上”前沿”的外衣招摇过市,理性的声音被喧嚣的炒作淹没。
回到最初与教授的对话,我们或许该达成共识:对AI的盲目乐观与悲观都不可取。作为科研工作者,最珍贵的品质是”实事求是”——既不夸大技术的潜力,也不否定其进步;既承认AI在信息处理上的优势,也清醒认知其与人类智能的本质差距。毕竟,科学的魅力不在于追逐”颠覆性突破”的虚名,而在于以严谨的态度,一步步逼近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