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福耀科技大学首届新生及家长见面会上,校长王树国的一番话引发热议 —— 他既鼓励新生主动与教授对接、培养主动性,又承诺学校会 “如家人般悉心呵护” 每一位学子。这番看似中肯的表态,却暗含着一对矛盾:大学本是学生 “社会性断乳” 的关键场域,是弱化亲子依赖、培养社会适应力的 “练兵场”,可 “如家呵护” 的承诺,却仿佛在为 “续奶” 站台。无独有偶,上海交大、同济、复旦等多所高校同期召开新生家长会,从报到时的 “全家总动员”,到家长群里追问学生动态,父母的干预正悄然渗透进大学校园,让本该 “断乳” 的阶段,沦为 “续奶” 的新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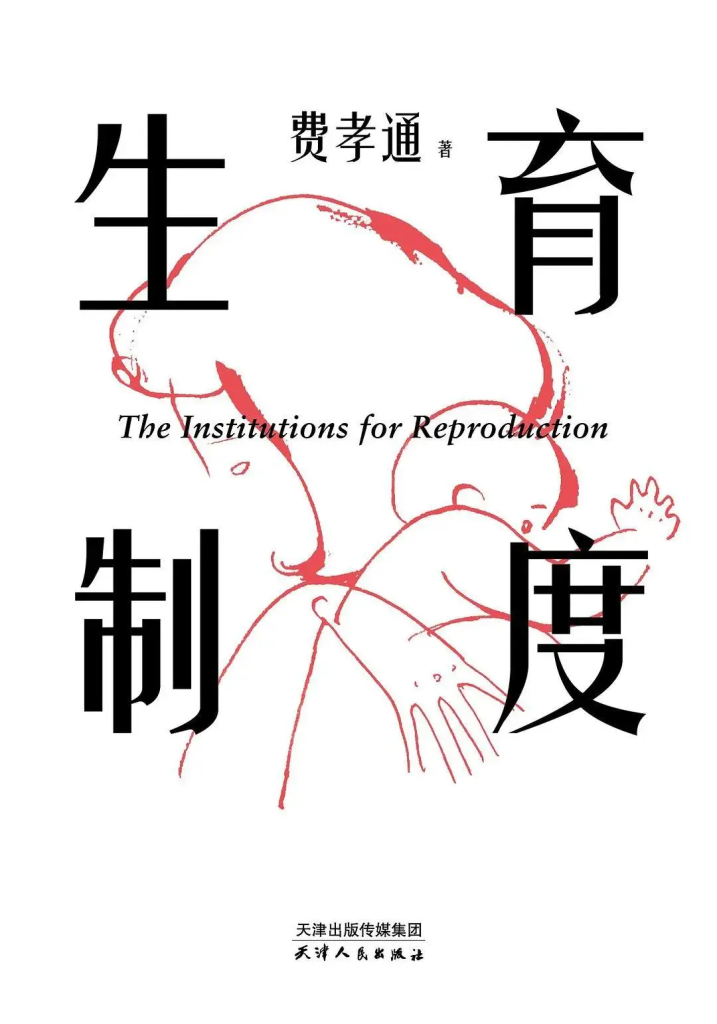
要理解这种矛盾,首先要回到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提出的 “社会性断乳” 概念。他在书中深刻指出,家庭本质是 “暂时性抚育场域”,核心功能是保障孩子在幼年获得保护与供养,而抚育的终极目标,是打破原生联结 —— 就像生命终将走向死亡,家庭抚育的终点,是让个体从家庭角色转化为社会角色,以维持社会结构的运转。人类幼年依赖成人的时间远超其他生物,父母天然会觉得 “儿女永远长不大”,可若任由这种心理延续,孩子会在家庭的 “迁就与谦让” 中,失去在社会竞争中 “斗狠” 的能力。费孝通笔下 “小市镇的少爷们”,正是长期待在家庭温室里的产物 —— 他们习惯了被成全,一旦进入 “你死我活” 的社会竞争,便会手足无措。
大学,本应是辅助 “社会性断乳” 的现代仪式。就像传统社会的成年礼,将 “父母的宝贝” 蜕变为 “能独当一面的战士”,大学的意义在于为学生搭建一个 “半社会” 空间:在这里,没有父母无条件的迁就,需要自己主动对接教授争取课题,需要自己处理室友矛盾,需要自己规划学业与未来。可如今,家长会的普及、家长群的建立,却让这个 “过渡空间” 逐渐变味。有家长要求辅导员叫孩子起床,有家长因孩子三天没发朋友圈便让老师去宿舍查看,甚至有高校在家长群里公布学生排名 —— 这些行为看似是 “家校联动”,实则是家长将家庭的 “监护权” 延伸到了校园,也让高校变相转嫁了管理责任,用 “呵护” 的名义,弱化了学生的独立性培养。
更值得警惕的是,家庭结构的暂时性,本就注定了 “亲子分离” 的必然。费孝通提出,“父 – 母 – 子女” 构成的家庭三角,只是阶段性存在,终将被子女建立的新家庭三角取代。若原有三角过于坚固,子女的成长便会受阻 —— 这也解释了为何高考后会出现 “离婚高峰”:当抚育使命完成,家庭的核心意义便会弱化。可在 “精密化育儿” 的当下,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六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转了 18 年,“放手” 变得异常艰难。家长们投入了巨额的情感与资源,将孩子视为 “最重要的资产”,自然不愿轻易放弃 “监护权”;而高校迎合这种需求,看似是 “关怀学生”,实则违背了高等教育的初衷 —— 大学不是家庭的延伸,更不是 “巨婴” 的温床,它本该教会学生如何对自己负责,如何在没有家人庇护的环境中生存。
这种 “续奶式” 的呵护,正在催生两种危险的结果:一种是永远长不大的 “巨婴”,他们习惯了被安排、被照顾,离开家长和老师的督促,便无法规划自己的生活;另一种是 “双面人”,表面上顺从家长和学校的安排,内心却充满叛逆,一旦脱离监管,便会陷入混乱。这两种情况,都与 “培养社会合格人才” 的高等教育目标背道而驰。费孝通曾反问:“除了父母,谁肯无偿地授予你他自己劳力的结果呢?” 家庭能给孩子 “任性” 的空间,但社会不会 —— 大学的价值,正是让学生提前适应这种 “不任性” 的规则,而非继续享受 “如家” 的特权。
事实上,“社会性断乳” 并非断绝亲子关系,而是建立新型的平等关系。它意味着学生要学会对自己的学业、生活、未来负责,不再依赖父母的安排;意味着家长要从 “管理者” 转变为 “支持者”,不再过度干预孩子的选择;意味着高校要收起 “如家人般呵护” 的温和姿态,多给学生 “试错” 的机会,让他们在挫折中学会成长。当学生能主动与教授沟通课题,当家长能坦然接受孩子的 “不完美”,当高校能坚守 “培养独立个体” 的初心,大学才真正能成为 “断乳” 的仪式场,而不是 “续奶” 的温室。
开学季的家长会,本不该成为 “亲子依赖” 的延续。大学四年,是学生从 “家庭人” 走向 “社会人” 的关键时期,需要的不是 “如家呵护”,而是 “战场练兵”。唯有当家长愿意放手,高校敢于 “放手”,学生才能真正完成 “社会性断乳”,成长为能在社会中独当一面的 “战士”—— 这,才是高等教育应有的模样。
